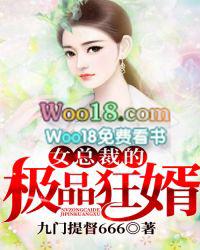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>夫人请住口 > 第308章 得罪他就算是得罪活阎王了求月票(第1页)
第308章 得罪他就算是得罪活阎王了求月票(第1页)
魏岳正在家中用晚膳。
孤零零的一人显得冷冷清清。
桌上只有一荤一素和一壶温酒。
相较于他的身份而言,这桌晚膳可以说是清简,甚至是上不了台面。
突然,魏岳抬头看去。
不消片。。。
我站在高台之上,风从永宁塔的方向吹来,带着铜管深处未散的余音。那声音低沉而绵长,像是无数人喉咙里尚未说出的话,在地底缓缓流动。我闭目倾听,仿佛又回到少年时第一次踏入回音廊的那个清晨??那时我还以为,只要听见,就能改变。
可如今我知道,听见只是开始。
“谢真人。”身后传来脚步声,是陆明远。他已不再穿巡言卫的黑袍,而是换上了青灰布衣,腰间却仍挂着那枚铁牌,上面刻着“直言无讳”四字。他说这是李木匠传下来的遗物,不能丢。
“‘无头林’今日醒了。”他低声说,“说了三句话:‘我要回家。’‘我不疯。’‘你们得记下来。’”
我点头,没有睁眼。“记下来了么?”
“记了。连同他指甲缝里的泥土都封存了??据验土师说,那是西山枯井特有的红壤,含铁量极高,与当年劫案路线图上的标记完全吻合。”
我睁开眼,望向远方。天边云层翻涌,像一场迟迟不落的雨。
“沈知微的尸身……还在衙中?”我问。
“昨夜抬去了义庄。他家人不敢认,说是‘辱没门楣’。裴少卿亲自去了一趟,带回了他的日记本。”
我转过身:“写了什么?”
陆明远从怀中取出一本薄册,纸页泛黄,字迹清峻如刀刻。“前三十页,全是公务记录,一丝不苟。第三十一页开始,有了变化。”他翻开一页,念道:
>**“永昌三年冬,舅父周廷章于肃静堂焚书自尽前,对我说:‘谢心亮不死,国不得安。然若你入言台,切记??莫做执刀之人,亦莫成遮耳之墙。’我始终不解其意,直至今日方悟:他恨谢氏,却也怕世人再无人敢言。”**
我心头一震。
陆明远继续念:
>**“我奉母命而来,欲清谢氏,可当我看见百姓跪在传声点前哭诉冤屈时,竟觉双膝发软。他们不信朝廷,只信言台;不求官老爷,只求‘谢真人听见’。若我毁此地,便是断万民之声。我既不能背师,又不忍欺心,唯有一死,以全两端。”**
最后一行字极小,几乎难以辨认:
>**“若有来世,请让我生为庶民,只说真话,不说使命。”**
我接过日记,指尖轻抚那行字,久久无言。
原来他并非没有挣扎。
原来他也曾站在深渊边缘,听见自己灵魂的撕裂声。
“烧了吧。”我说,“不必公之于众。”
陆明远迟疑:“可这能洗清他的污名。”
“他不需要被洗清。”我摇头,“他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??在忠诚与良知之间,选择了沉默的承担。这种人,最不该被拿来当作辩白的工具。”
陆明远默然收起日记,转身欲走,却又停下:“裴少卿说,内务府昨夜失火,御药房残卷……不见了。”
我冷笑一声:“果然来了。”
“您还打算追吗?”
“当然。”我望着天际,“赵德安贬为庶民,但他的亲信仍在宫中。先帝用药之事虽被轻描淡写,可那份凭证投影天下,已有百余名御医联名上书,请彻查‘忘忧散’配方来源。只要线索不断,火就不会灭。”
他点头离去。
我独自立于高台,手中握着那块素荷留下的桂花糕干皮。它早已脆如枯叶,稍一用力便会碎裂。可我仍舍不得扔。就像那些年她藏在我案头的温茶、掖在我肩上的披风、夜里悄悄替我续写的《补遗录》手稿??她从未想让我知道她做了多少,可我知道。
风忽然大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