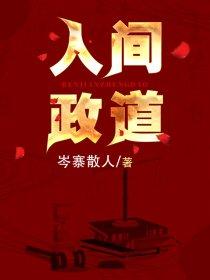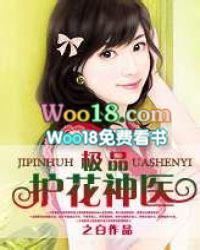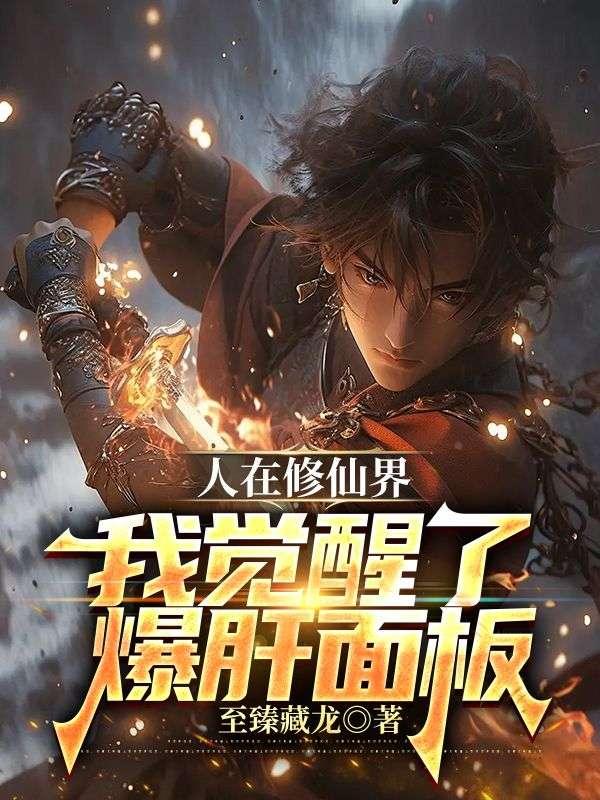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>重生之按摩师的自我修养 > 第103章 孩子留一条后路吧(第2页)
第103章 孩子留一条后路吧(第2页)
她站起身,走到窗边拉开一道缝隙,让晨风灌入。阳光斜切进来,照亮空气中漂浮的微尘。
“接下来,我们要处理更深层的部分。”她说,“你带来的那件衣服,可以拿过来了。”
我照做,将校服平铺在床上。
她让我把手放在衣服上,闭眼回忆母亲缝补的那一夜。
“她说什么了吗?”她问。
“她说……‘破了就补,人也是。’”我喃喃道,“我还嫌她针脚丑,说以后买新的。”
陈默轻笑:“可你一直留着。”
我哽住。
她忽然伸手,指尖轻轻划过我左胸第三根肋骨下方??一个我自己都未曾注意的位置。
“这里,有一道‘否定印记’。”她说,“很小,但很深。它来自童年某次被重要之人否定核心价值的经历。比如你说想画画,却被父亲说‘不务正业’;或者你想哭,却被母亲训斥‘男子汉不能软弱’。”
我猛地睁眼。
七岁那年,我在学校绘画比赛拿了二等奖,兴冲冲跑回家给父亲看奖状。他扫了一眼,冷冷道:“美术能当饭吃?以后少花时间在这种事上。”
那天晚上,我把画撕了,扔进垃圾桶。从此再没碰过彩笔。
“你怎么知道?”我声音发颤。
“因为你的呼吸模式暴露了它。”她平静地说,“每当触及自我表达的主题,你会下意识屏息半秒。那是心理盔甲启动的信号。”
她让我重新躺下,这次要求我穿着校服。
然后,她开始按摩我的背部??不是肌肉,而是沿着督脉和膀胱经的特定穴位,以极轻的抚触进行刺激。每一次触碰都像在点燃一根微弱的火柴,照亮一段被遗忘的记忆。
我看见十岁的自己站在演讲台上,准备念作文《我的梦想》,台下老师微笑鼓励,同学鼓掌期待。可话筒刚拿到嘴边,脑海突然空白。我僵在那里,脸涨得通红,最终低头跑下台。第二天,班主任找我谈话:“吕程,你逻辑能力强,适合学理科,文艺方面……就算了吧。”
那一句“就算了吧”,成了我此后二十年回避一切公开表达的潜意识指令。
“他们不是恶意。”陈默一边按一边说,“但他们用‘为你好’的名义,切断了你与真实自我的连接。而你的身体,替你记下了每一次断裂。”
我泪流满面。
不是控诉,而是理解。原来那些我以为靠意志克服的怯懦、疏离、冷漠,不过是层层包裹伤口的茧。
疗程结束前最后十分钟,她让我坐起,面对她盘腿而坐。
“现在,请你用手,触摸自己的胸口。”她说。
我迟疑着照做。
“感受那里的心跳。不要评判它快或慢,强或弱。只是看着它,像看着一个受过伤的孩子。”
我照做。
渐渐地,一种久违的柔软从胸腔扩散开来。我意识到,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,真正“看见”自己的存在。
“恭喜你。”陈默微笑,“你完成了第一次躯体记忆释放。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机会做这件事。”
我哽咽难言。
离开前,她递给我一张卡片,上面写着一行字:
【下次预约将在14天后。期间请每日记录三次身体感受,无论喜怒哀乐。】
我走出柏翎疗域,阳光洒在脸上,街道喧嚣扑面而来。可世界不一样了。车流不再刺耳,人群不再压迫,连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的强光,都像是某种温柔的注视。
手机震动,彭琴发来消息:
“怎么样?”
我回复:“她没按我的肉,她按了我的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