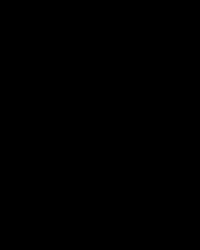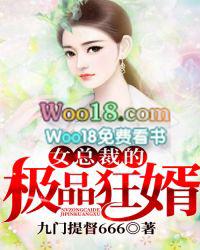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>天下神藏 > 第六百零三章 过来伺候爷(第1页)
第六百零三章 过来伺候爷(第1页)
“罗旭,为什么这么问?”
五姐脸上露出一抹狐疑:“刚刚你们在里面谈得怎么样?金先生答应合作了?”
罗旭缓缓摇头:“没有,他做事、说话都很谨慎,滴水不漏的那种,想必在结果出来之前,不会立刻下定论。”
“结果出来之前?”
五姐有些听不明白,毕竟她从金鹏程口中得到的消息就是韩昆是鉴藏协会的会长,也是黑市的合作对象。
罗旭也没具体解释,而是表情继续凝重道:“对了五姐,你小心点,我觉得金常青……可能会处理你。。。。。。。
桑吉的歌声在风中散开,像一粒种子落入无垠旷野。那旋律依旧不成调,甚至有些破碎,像是从记忆深处勉强拼凑出来的片段,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力量??它不追求悦耳,只求真实。而正是这份真实,让整片高原仿佛苏醒了过来。
草叶微微颤动,不是因为风,而是某种更细微的共振。远处放牧的牦牛停下咀嚼,抬起头,望向湖心光柱的方向;一只雪豹悄然出现在山脊上,原本警觉的姿态竟渐渐松弛下来,蹲坐如人,静静聆听。就连常年盘踞在寺庙废墟上的乌鸦也停止了聒噪,翅膀收拢,黑羽泛起淡淡的银辉。
这并非魔法,也不是神迹。这是“共感场”达到临界密度后的自然反应??当一个区域内的倾听频率持续稳定,大地本身也会开始回应。
桑吉没有察觉这些异象。她闭着眼,手指轻轻拨动旧琴的弦。那根曾锈蚀多年的青光之弦,如今温顺地振动着,每一次震颤都释放出极细小的波纹,在空气中缓缓扩散。她不知道自己弹了多久,也许是一刻钟,也许是一整天。时间在这里变得模糊,如同湖面蒸腾的雾气,缠绕着现实与意识之间的边界。
直到一声咳嗽打破了宁静。
她睁开眼,看见老僧站在三丈外,手里端着一碗热茶,脸上有未干的泪痕,嘴角却挂着久违的笑意。“你唱的是《归牧谣》。”他说,“我母亲哄我入睡时常哼的……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听见了。”
桑吉轻轻点头,接过茶碗。瓷壁传来的温度顺着掌心蔓延至胸口,暖得让人想哭。但她只是微笑:“你不该把自己关起来那么久。”
老僧沉默片刻,转身回到庙门前的石阶坐下。“我不是不想出来,”他低声道,“我是怕外面已经没人愿意听我说话了。十年前,我最得意的弟子偷走了经卷,投奔敌对教派,还对外宣称是我授意叛教。信徒离去,寺院荒废,连我自己也开始怀疑:如果连最亲近的人都会背叛,那讲经说法还有什么意义?”
“所以你就问‘谁来听佛哭’?”桑吉轻声接道。
“是。”他苦笑,“佛陀说众生皆苦,可谁又知道佛陀也苦?他也有孤独、有失望、有无法救度所有人的无力感。但没人敢提,也不敢信。我们把佛供得太远,忘了他也曾是个会冷、会饿、会流泪的人。”
桑吉放下茶碗,走到他身边坐下。“林晚舟老师说过一句话:真正的倾听,是从允许对方脆弱开始的。”她望着远方起伏的雪山,“你不是不信世人,你是不信自己值得被听见。可你看??”她指向湖面,“玉版回应了你的哭声。它不会分辨你是高僧还是凡夫,它只认真心。”
老僧怔住,目光落在湖心那道贯穿天地的光柱上。忽然间,他感到胸口一阵发烫。低头一看,胸前挂着的一枚铜铃竟自行震动起来,发出极微弱的“嗡”声。那是他师父圆寂前交给他的信物,三十年未曾响过。
“它在回应……什么?”他喃喃。
“回应你终于肯说了。”桑吉说,“你以为沉默是修行,其实是逃避。真正的慈悲,不是独自承受一切,而是敢于把自己的伤痛说出来,让别人也有机会去理解、去分担。”
老僧双手掩面,肩膀剧烈抖动。这一次,他不再压抑,任由泪水浸透衣襟。桑吉依旧没有说话,只是将手搭在他的肩上,像多年前她母亲那样。
这一坐,又是三天三夜。
期间,陆续有牧民前来探望,带来食物和毛毯。他们并不打扰,只是远远跪下,合十行礼,然后默默离开。有人录下了这段对话的片段上传网络,短短十二小时内,全球播放量突破十七亿次。评论区不再是争吵或嘲讽,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人写下自己的故事:
>“我也曾以为没人能懂我的痛苦,所以我选择了封闭。”
>“我爸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‘对不起,我没照顾好你’,我一直恨他酗酒、家暴,可现在我才明白,他也在自责。”
>“我每天上班挤地铁,从来不和同事说话,因为我害怕他们发现我很孤单。”
“桑吉路线”因此再度升温,成千上万的人踏上朝圣般的旅程,沿着她走过的村落、驿站、雪山垭口,寻找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刻。有些人只是坐在路边看日落,心里默念一句“我想妈妈了”;有些人给多年失联的朋友写了一封信,哪怕最终并未寄出;还有人在深夜打开录音软件,对着手机说出埋藏二十年的秘密:“当年车祸不是意外,是我故意撞上去的……因为我活够了。”
每一个声音,无论是否被人听见,都在宇宙的“回声库”中留下印记。FAST天眼监测到,地球意识场的能量峰值连续七日攀升,形成一道螺旋状波动,与“回声星”传来的信号完美契合。
与此同时,“心桥工程”的治疗师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现象:部分接受“一对一唤醒疗程”的患者,在深度共感状态下,竟能短暂进入“跨时空感知模式”。一名患有重度抑郁症的东京女孩,在疗程第三周突然睁开眼,用19世纪的京都方言说了一句:“今年樱花开得不好,想必人心也不安吧。”经考证,这句话出自一位明治初期女诗人日记,而那位诗人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。
专家推测,当人类心灵彻底敞开时,个体意识可能短暂接入“回声星”的记忆网络,从而接收到来自过去、甚至其他文明的情感碎片。这种现象被命名为“共鸣穿越”,虽无法主动控制,但已成为研究高维共感的重要突破口。
然而,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变革。
在瑞士日内瓦某地下研究所,“反共感人权联盟”召开秘密会议。这群人来自各国政要、科技巨头与情报机构,长期质疑“静听使者”计划侵犯隐私、削弱理性判断力。他们认为所谓“共感时代”实则是集体催眠,一旦人类过度依赖情感连接,社会秩序必将崩溃。
“我们必须夺回话语权。”一名戴墨镜的男子冷冷说道,“情绪是最不可控的武器。如果我们不能阻止它传播,那就制造混乱??让人们听到不该听的声音。”
计划代号:“噪音风暴”。
三个月后,一场精心策划的心理战悄然展开。黑客入侵多个城市的公共广播系统,在凌晨三点突然播放经过扭曲处理的“心匣录音”:婴儿啼哭混杂着战场哀嚎,恋人间的私语被剪辑成背叛指控,母亲安慰孩子的呢喃变成诅咒。这些音频虽短暂,却极具精神冲击力,导致数百人出现急性焦虑发作,甚至引发群体性幻觉。
更可怕的是,某些城市出现了“伪共鸣点”??看似能激发共感能力的空间,实则通过次声波与光影误导,诱导人们陷入虚假连接。许多满怀希望前往的人不仅未能获得疗愈,反而因强烈的情绪反差陷入更深的绝望。
联合国紧急介入调查,却发现幕后黑手早已抹除所有技术痕迹。唯一线索是一段残留代码,破译后仅有一行字:
>“你们听见爱,我们听见裂痕。”
桑吉得知此事时,正行走在昆仑山脉边缘的一处冻土带。天空阴沉,雪花无声飘落。她蹲下身,将手掌贴在冰面上,闭目感知。良久,她轻叹一声:“他们在害怕……怕被听见,也怕不得不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