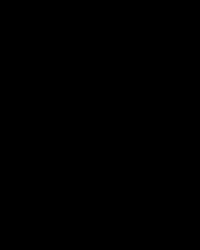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>只是力气大,你们怎么叫我祖宗 > 第三十八章 身世(第2页)
第三十八章 身世(第2页)
深层组织修复和神经活性恢复速度,是之前的数百倍!
按照这个趋势,最多一周,他就能恢复意识,
一个月内,有望下床进行简单活动!
这……这简首推翻了我们之前所有的预估模型!”
这时,杨老的声音从扩音器传来,带着笑意和无比的欣慰:
“好!太好了!周七啊,你又立了一大功!
不仅救了父亲的命,还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!
好好休息!你父亲这边,有最好的团队守着,你放心!”
我点点头,看着床上安睡的父亲,心里那块最大的石头,终于彻底化开了。
爹,快点好。
等你醒了,
咱们爷俩,
有的是“家常”要唠。
还有那些害咱们的账,
也得一笔一笔,
算清楚。
几天后,在我每日稳定的“同源能量滋养”下,容镇岳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。
虽然依旧消瘦,但脸上己有了血色,眼神也重新变得清明锐利,
只是深处沉淀着经年累月的痛苦与沧桑。
这天下午,阳光透过特殊材质的窗户,柔和地洒在干净整洁的独立病房内。
林予提前协调好了,这是一次绝对私密的会面,只有父子二人,
连监控和录音都暂时关闭(当然,外部仍有最高级别的安保)。
我坐在父亲病床边的椅子上,看着他。
他靠坐在升起的床头,也静静地看着我。
空气很安静,只有仪器规律的、轻柔的滴答声。
没有抱头痛哭,没有激动的呼喊。
一种奇特的、源自血脉深处的平静和默契,流淌在我们之间。
我体内的“虫子”和他心口的“蛊王”,似乎也在安静地共鸣着,传递着温暖而安稳的波动。
良久,父亲先开了口,声音还有些沙哑,但很清晰:
“像你妈妈。尤其是眼睛。”
他伸出手,似乎想碰碰我的脸,但在半空中停住了,只是仔细地看着,
“也像我年轻的时候,轴,认死理。”
我没说话,等他继续。
“我并不知道我有个儿子,我和阿月失散后的第二年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