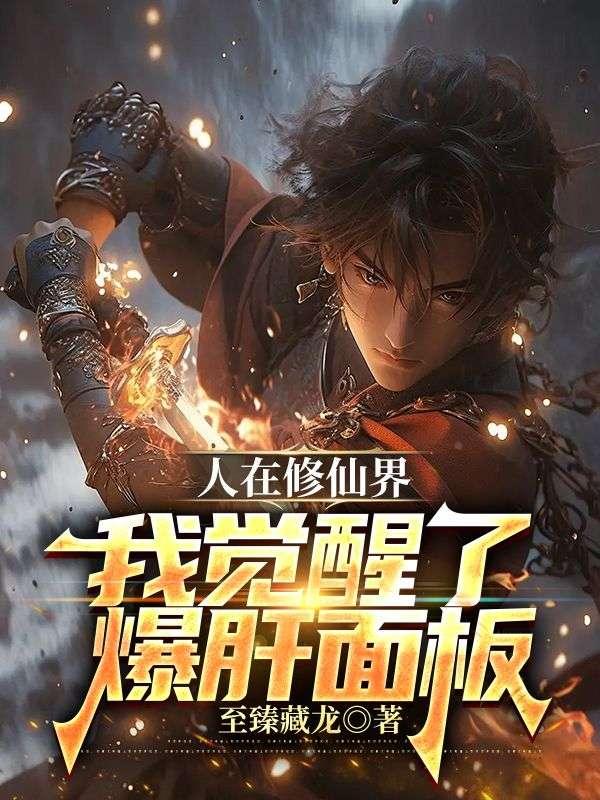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>我真没想霍霍娱乐圈 > 538章你是我唯一的姐(第2页)
538章你是我唯一的姐(第2页)
他把信打印出来,贴在厨房冰箱上,正对着那朵用雾气画过的花。每天做饭时都能看见。
春天再度逼近,城市解冻,冰凌滴水如钟摆。他开始筹备新剧《静息》,主题是临终关怀与生命尊严。主角是一位hospice医生,名叫陈默,四十岁,未婚,常年住在医院值班室。剧本第一场戏设定在太平间外的走廊,他蹲下身,帮一位刚去世的老太太穿好鞋袜,轻声说:“您走得体面些,孩子们才敢好好看您最后一眼。”
这不是虚构。原型来自他在老年康复中心认识的一位真实医生。那人告诉他:“很多人怕死,其实是怕被人遗忘的方式。他们不怕闭眼,怕的是闭眼前没人认真看过他们一眼。”
剧本写到第五场时,他收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回函:经全球专家评审,《神雕?归来》《记得》及其衍生社会行动,正式纳入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”,类别为“艺术驱动的社会共情实践”。函件特别强调:“这是该名录首次授予非传统艺术形式,因其展现出文化作品超越审美功能,直接介入人类精神修复的独特价值。”
他看完,把函件锁进抽屉,没告诉任何人。
他知道,真正的遗产不在奖章里,而在那些悄然改变的选择中:一个女人终于报警控诉家暴;一个少年撕掉休学申请,走进心理咨询室;一位父亲在儿子婚礼上第一次说出“我爱你”。
三月中旬,云南盲童合唱团寄来新专辑母带,名为《风中有声》。封面仍是孩子们集体绘制的画:悬崖之下,溪流蜿蜒,一人提灯涉水而来,另一人站在对岸,伸手相迎。内页多了一行新字:
>“以前我们以为黑暗是终点,后来才知道,它是光的形状。”
随信附有一段音频,是小姑娘的独唱试音。她唱的是《天上有双》改编版,歌词由孩子们共同填写。其中有两句让他怔住:
>“我看不见蓝天,但我听见它在风里飘荡,
>我没有翅膀,但我的心已飞过群山。”
他听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窗外暮色四合。
当晚,他梦见师弟站在麦田尽头,这次终于看清了脸。他笑着,像从前一样拍他肩膀:“哥,咱们当年说要做的那件事,做到了。”
“哪一件?”
“让那些说不出话的人,也能被世界听见。”
他点头,眼眶发热:“是啊,风一直在传话。”
醒来时,天未亮。他起身写下新剧《静息》的最后一场戏:
>夕阳西下,病房只剩微光。
>老人弥留之际,突然睁开眼,望向窗外。
>陈默轻声问:“您看见什么了?”
>老人嘴角微扬:“我老婆……在门口等我呢。她穿着结婚那天的旗袍,笑着说‘让你久等了’。”
>陈默握住他的手:“那您去吧,别让她站太久。”
>老人点点头,闭上眼,呼吸渐缓。
>镜头缓缓拉远,窗外樱花飘落,一片恰好落在窗台,像一封迟到的情书。
>画外音响起,是一位年轻女孩的声音:
>“爷爷,我考上医学院了。
>我想成为像您一样的人,
>在别人生命的最后一程,
>做那个认真听他们说话的人。”
写完最后一个句号,他长舒一口气,仿佛卸下千斤重担。
他知道,这部剧依然不会爆,依然会被批“太沉重”“不适合大众”。但他也清楚,总有人需要它??那位在ICU外守了三天的儿子,那位刚刚签下放弃抢救协议的女儿,那位每天面对死亡却不敢流泪的年轻医生。
他们不需要煽情,只需要一句:“你的痛苦,有人懂。”
几天后,《静息》项目书提交国家艺术基金。评审会上,有委员质疑:“这类题材是否过于边缘?能否产生广泛影响?”
李鸿泽起身回答:“如果一部剧能让一个人在绝望时多撑一天,它的影响就不算小。我们评判作品的价值,不该只看它赚了多少,而要看它救了多少。”
会议室安静了几秒,随后掌声响起。
立项通过。